作者 | 赵淑荷
发自云南昆明
编辑 | 谢奕秋
周二是张秋子一周里最忙碌的一天。
这个学期,每周二的下午,她带学生一起读卡夫卡,傍晚讲库切,20时以后,是果戈里的《鼻子》。三堂大课中间有一个短暂的用餐时间,她总是跟固定的几个学生一起吃饭,他们有一个读书小组。
晚饭结束,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学校外不远的云南省科技新馆着火了,滚滚黑烟直升昆明的湛蓝天空。张秋子站在食堂的楼梯上陷入百爪挠心的回忆:有一本书里写了着火的时候很多人在一旁围观的场景,是哪本?
晚上9点半,秋子上完了一天的课,她跟小组成员一起绕下教学楼长长的楼梯,在湿凉的夜雨中,她有些雀跃:“我想到了,那本书就是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2016年,从南开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张秋子回到家乡,成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高度集中的、与生活同一的文学阅读生涯同时起步。2022年,她出版了文学随笔文集《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此后,她把文本细读的手艺跟更多的读者分享。书的腰封上写“赛博领读人”,秋子有点惭愧,更愿意称理想中的自己为“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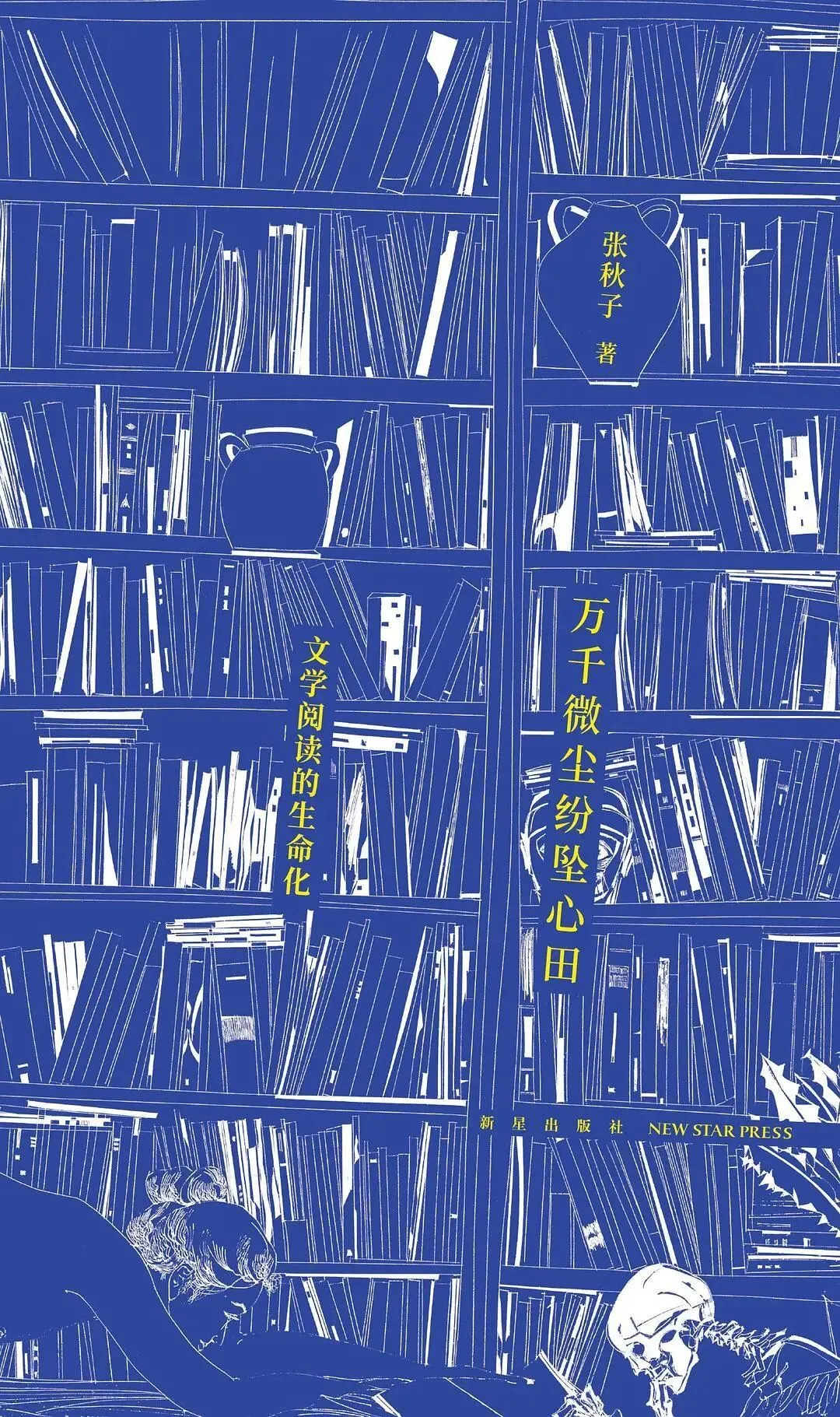
《万千微尘纷坠心田》
9月,我联系到秋子。抵达昆明后,我上了她周二的文学课,跟她在云师大的食堂吃了两顿饭。
秋子保持着一种勤勉的读书生活,单纯的投入让她看起来仍像一个学生,长长的直发披在牛仔服上,帆布袋和鞋子呼应颜色,此外没有任何修饰。
她问我看什么书。这是秋子了解一个人的方式。每年学期初,她让同学们作自我介绍,但不是“我叫什么”“我几年级”那种,而是让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的阅读史。借用一句英语谚语,在秋子的世界里,you are what you read。
阅读塑造了她,塑造了她的学生和读者。
周二的文学课
张秋子是一个严厉的老师。
她在课上点名,超过两次没有出席的学生,“下次也就不用再来上课了”。每学期初,她会先劝退学生,因为在这门课上绝对不能划水,如果你只是想用最经济的方式弄到两个学分,她的课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想跟她一起领略文学魅力,那么她会毫无保留地向你敞开,连带着那个令她流连忘返的文学世界。
在秋子的影响下,她的学生会习惯用“文本”而不是“书”来指代他们阅读的对象,即便是来旁听的学生,落座时也会问旁边的同学:“请问这节课读的文本是什么?”
一些在大三上过秋子的文学课的同学,大四还会来上,为了跟秋子一起读新书。
通过故事和人物,秋子把那些艰深的理论在巨大的word文档投屏上展开,引申出不同学科的先贤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以赛亚·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德里达的延异,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警惕犬儒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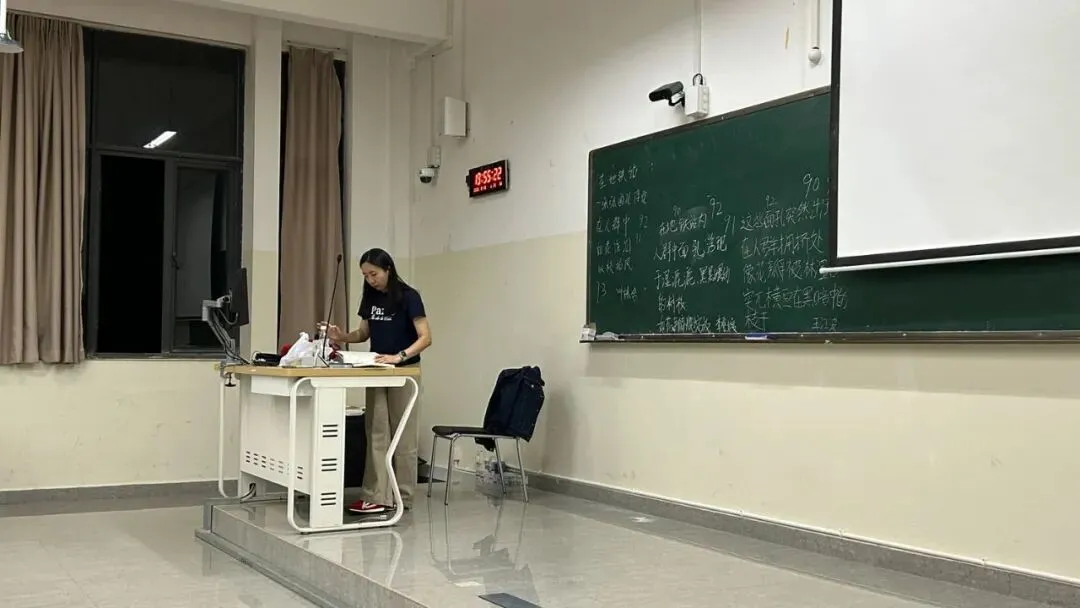
张秋子/赵淑荷 摄
理论是托举文学的脚,通往日常生活。理论的普遍性能够帮助我们与新的具体情境和文本相遇,从新的经验里,我们再次走上理论的高度。在这种“反复横跳”当中,秋子和她的学生正在接近理想中,“文本中的平衡和突围”。
周二下午的课读《城堡》,课上一个男生发言,说起他和同学们曾经为拿到一份成绩报告,不得不在各个看起来完全无关的办公室之间奔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卡夫卡时刻。
人和文本如何发生关联,会激起阅读者的好奇心,接下来,则是智性活动被唤起。张秋子用Keep软件的slogan“自律给我自由”来讲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用大学生的处境来讲“犬儒主义”——一个明知自己无论怎样学习都找不到好工作的普通一本学生,可以因此就放弃求知吗?“把你自身的一个小的落脚点,往生命更完整的状态上去沉思。”她在课上拿祥林嫂当反例说,“我们不要无意识地抱怨,我们要进行有意识的、持续性的实践。”
《城堡》里的阿玛丽亚,是张秋子最喜欢的文学形象之一。在城堡里的其他女性以向城堡高层提供性服务为荣的时候,阿玛丽亚拒绝这样的安排,在《小说榫卯》中秋子解释:“这个角色是文学中最接近古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形象的女性,她们都代表了一种罕见的人类美德:不屈从。”这种天性最开始在她体内只是模糊的一团物质,然而,“当我遇到卡夫卡之后,它的轮廓突然清晰了”。

跟她一起,很多孩子开始在课堂上思考,他们要如何面对生活做出选择。最近经常被秋子和学生们提起的一个例子是参加没有意义的考试。很多学生去做,但是抱怨;有的学生则选择不去参加;还有的学生去了,但是在试卷上瞎写一通。
秋子说,如果是她,她一定选择不去。但是瞎写的学生,她也赞赏,他们在课上提到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微小的抵抗也是抵抗,是一种“艺术”。
我问秋子,今年选择的文本似乎都涉及权力的运作,这是否跟她一个阶段内关心的议题有关?
“权力只是表层,透过它的运作,我们最终要讨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选择或者如何生存。”
K面对城堡,迈克尔·K面对南瓜,默尔索面对死亡,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对罪行——人怎样选择自己的存在,是所有文学都在关心的问题。
审美和智性愉悦
在文学阅读上,张秋子是个“技术流”。
借乔纳森·克拉里的那本《观察者的技术》,我对秋子说,她在文本细读上的耕耘展现出一种“阅读者的技术”。
秋子没有否认,只是温柔地补充:“技术也还是要有感受作为打底。”
在秋子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体会这一点:当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感知和思考个体进入文学,文学会给你回报。

张秋子在课堂上/赵淑荷 摄
秋子最近感受到的回报,来自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是读书小组的伙伴分享给她的书,其主题是很多现代作家已经放弃探索的问题,“人的救赎”。主人公放弃美国的城市生活去贫困地区给妓女传教,最后在带着妓女去打官司的路上被车撞死了。
“一个圣徒。”当她看到一个当代作家仍然在讨论人身上有可能出现的神性,她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但她不希望这种神性被理解成一种高度戏剧化的东西,它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闪光,可以借由微小的努力达成,是“从平凡走向超越的可能的实践”,是“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种向上的努力”。
张秋子的“微信读书”显示,她每天最少读书4个小时,纸质书要另算,所以她估计自己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是6个小时。她会同时读五六本书,全部读完之后,一口气写完这些书的短评。在这个人人觉得自己读不进书的年代,张秋子的烦恼却是“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沉迷阅读了”。在学校门口等待记者的5分钟里,她在读前一天上课时一个女生提到的《弱者的武器》。

《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在阅读中流连忘返的张秋子,总是想告诉别人“读书为什么快乐”。
张秋子经常用的一个词是“推论”,她要求学生缜密和充分地推导自己的结论,也常常通过推论来帮助自己和学生去理解比较深奥的概念,这个过程会给人带来智力的满足感,一种“审美和智性的愉悦”。
她在课上讲果戈里的《鼻子》,主人公丢了鼻子到找到鼻子间隔了12天,俄罗斯历法儒略历和欧洲历法格里高利历也隔了12天,由此秋子推断,果戈里用主人公的命运来讲俄罗斯/彼得堡的命运。主人公在小说里过了两种生活,有鼻子的生活和没有鼻子的痛苦的12天,而这个故事发生在彼得堡,这个城市是彼得大帝西化的结果,所以果戈里在写俄罗斯本土文明与西欧文明的落差。
这个解读未必是“正确的”,它不一定是果戈里的真实想法。但是它有成立的基础,符合语境,张秋子感到兴奋,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发现发给一起读书的学生。
张秋子把手里的两份论文开题报告给我看,她很满足,“今年指导的学生写的题目都很好玩”。其中一个学生写《复活》里的“徘徊”,就是人物在故事里经常走来走去独自踱步,这个学生去看那些研究“行走的历史”的文献,发现它不止是一种常见的肢体行为,它是一种动物不具有的行动,也是人得以与大地连接的方式,“徘徊”有很深的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复活》,“他写得很好”。

图源:Unsplash
在一个庞大、经典的文本当中找到新鲜独特的切入口,一定倚赖精细和富有创造性的阅读。秋子不允许她的学生“套理论”,《××理论视域下的××》这样的题目在她这里不会通过。她希望学生能够冲破理论的迷雾,真正与文本“贴身肉搏”,感受自己与文本的互动。
这个过程对很多学生来说并不容易。秋子在课堂上,总是要求学生在文本中抓一个细节去阐释,如果说不出来,那至少提一个问题,如果问题也没有发现,“那你就告诉我你在哪句话下面划线了,回忆一下,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划线?”
张秋子不希望自己跟学生之间不断生产高校教育中常见的“假对话”,一方说话,另一方说“好的不错请坐”。她以一种助产士式的逼问,尝试唤醒孩子们学习的本能,困惑、疑问、质疑、反思,这些都是在基础教育和陈词滥调中有可能被磨灭的能力。
不止于文学阅读,它同时是对人学习思维的一种锻炼。最近的课上,开始有学生念出AI的答案来应付秋子的提问,秋子一听就听得出来。她说,你把这些回答抛开,哪怕说出你的困惑,也比这个完美的答案要好。
文本细读是一种诚实的阅读。它唤起的是一个人与文本真实的互动,你需要在面对文本的时候坦诚严肃地面对自己的感受,去倾听自己的声音,最后是你要相信自己,你的感觉和表达是有意义的,“很多时候人们太看轻自己的感受了”。
把生命的感受嵌入文本,你就有可能达到一种创造性的阅读。作家本人可能并没有设计这些意图,但是你可以不停地使用你的想象力在你的知识结构里进行推论,这是“自我创造的积极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秋子认为不存在“过度解读”,这个说法预设了阅读有“度”,她微微抬起素净的圆脸看向我,“请问度在哪?”
阅读和批评完成了对一个文本的再次书写。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可以与彪炳史册的巨著和青史留名的作家平等对视,你可以创造《复活》,创造《罪与罚》,创造《包法利夫人》,这是阅读者的权利和能力。
阅读中的共同体
周三的外国文学史课上,秋子讲古希腊史诗。
《奥德赛》里有一个情节,是说奥德修斯漂到一个岛上遇到独眼巨人,这个巨人独居,吃独食,最后被打败。在秋子的理解中,某种意义上,这个角色意味着古希腊人认为孤僻的生活是不可取的,城邦精神期待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她对文学批评的另一种期待,就在这个层面上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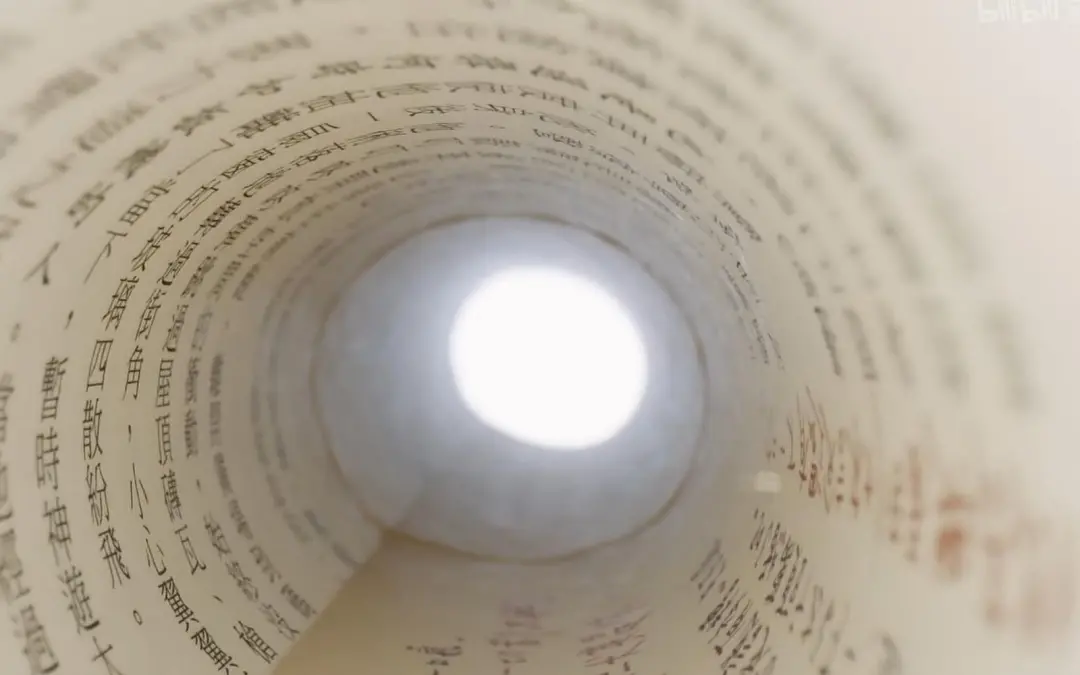
《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在第一本书里,她追问阅读的“效用”,找到两个答案:督促人成为人,以及推迟判断。前者需要真实感受,后者指向文学的多义和宽容。最近,她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文本可以作为一种中介,最终走向对人的关系的实践”。近十年教书生涯里,除了在文学理解上的进益,这也许是她最大的收获。
“因为有课堂的存在,我们形成了一个特别亲密的智性的共同体。”在课堂上共同针对一个文本发生情感和知识的沟通,被秋子视为一种人与人在智力上走向亲密和相互扶持的新的可能。
跟学生一起从食堂走向教学楼的傍晚,在丛丛植物掩映着的暮色当中,秋子和这些亦师亦友的伙伴提到了一个动词:辨认。
采访当天,她补充了对这个词的解释。辨认是友谊的开端。她和爱阅读的孩子们彼此认出,然后很快地建立信任。她在写一本记录这种友谊的非虚构作品,才发现自己过去从没有好好思考过友谊,“它不依靠血缘,也不依靠身体,这是唯一一种依靠我们的精神走到一起的关系模式,而且它是开放的”。

2024年8月3日,福建厦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图书馆/施泽科 摄
一个经常发生的场景是,秋子读到了很好的小说,“强烈安利”给同学们,大家都读完之后,约在奶茶店,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拿出书来,开口已经在讨论里面的情节和文句,没有任何铺垫,“迅速地进入彼此相信对方的品位和判断的世界”。
这个小组里当然每年都会有毕业的学生,但他们仍然因为文学保持密切的联系,读书时爱写诗的学生现在仍然爱写诗,还是会发给秋子看。正是这种客观的变动让秋子更加相信,“这个共同体不依靠面对面的接触维系,它是依靠我们之间相似的内在性形成的”。
2022年,张秋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文学阅读超出了课堂,借助出版业和现代媒介走向了更多人,于是这个共同体的建构也有了更大的可能。
秋子经常在新书活动、校外讲座里,遇到一些让她觉得很熟悉的读者,有学生,有白领,他们会跟秋子说,读书的时候,感觉自己不孤单。秋子想起大学的自己,经常因为在读书当中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伙伴而感到失落,于是这种“认出”令她备受鼓舞。她常常在扉页为读者写下一句to签:“走向你的同类。”
很多人认为在这个时代读书变困难了,但秋子相信,读书的人既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少。尽管你放眼望去好像所有人都在刷短视频,但阅读制造的共同体会让你知道,在角落里总有一个人在读书,文学会把你们磁吸在一起。
每一个对知识有信念和渴望的人,会努力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朋友。

《但是还有书籍 第三季》剧照
张秋子经常推荐学生们去云南大学听袁长庚的课。她和袁老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借袁老师的话来说,他们都对学术体系内部的生产和成就毫不上心,唯二追求的事物,“一是知识本身,二是把知识传播出去”。
在人文学科执教的年轻教师们,每年都要处理学生的“幻灭”和“失落”,无论是对一个普通的双非院校本身,还是对文科学习,对那个在网络上被反复讨论的充满焦虑的未来。
就是从这个层面出发,知识本身才更有力量。
袁长庚会跟学生说,可以对大学幻灭,但是不要对知识本身幻灭。
张秋子非常认同这一点。
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