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龙女 于 2024-3-7 23:35 编辑
拒绝“女神节”,拒绝“女王节”,三月八日最美好的名字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这又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类型,每逢三八妇女节,只要“女神节”“女王节”的歪风还在,我就要再说一遍。
“三八妇女节”起源于1857年3月8日的美国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女工们随后成立了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此后每年的3月8日,从纽约到芝加哥,从英国到俄罗斯,都有此起彼伏的妇女运动来纪念响应、纪念这次罢工。1921年,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妇女代表的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国务院就颁布规定:妇女节(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妇女放假半天。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也会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然而随着年代的渐行渐远,“妇女节”这一称谓也逐渐淡化。近年来在互联网电商巨头们的推波助澜之下,诸如“女神节”“女王节”“女生节”等成为大行其道,仿佛“妇女”二字已经被人羞于提起。往年京东是女神节、淘宝是女王节、小红书等平台是女生节;后来反对声音太多,淘宝改成叫“三八节”,京东改成了“她的节”,虽然也避开了“妇女”二字,但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平台虽然改了,品牌和商家依旧沿用着“女神节”“女王节”等荒诞不经的名称,还有各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广告宣传行为。
2019年3月8日,主打女性超级英雄题材的《惊奇队长》在中国上映,女主角的祝词也是“女生节快乐”。虽然那次主要是国内宣发自作聪明,但是超级英雄片伪善的政治正确是一贯的,就好比《黑豹》主打黑人超英,结果里面的非洲各种固化印象,只是给弱势群体一种精神鸦片式的满足,并没有着眼于真正的平等与权益。
为什么好莱坞的政治正确是伪善的?为什么电商巨头们的女神节、女王节必须批判?为什么说这不是女性真正的平等与权益?因为妇女节的关键在于“劳动”二字。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天然的盟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加强化了父权制。首先,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而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财产所有者和继承者,往往是男性。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想要成功,必须将人——特别是女性定义为消费者,用消费主义去洗脑她们,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剁手买买买、通过日益增长的物欲与消费——而不是在生产劳动中去实现。
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一方面来自父权制的精神奴役,比如京东美妆的那一句广告语:“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来自于伪女权的自我洗脑,比如“买买买才是女人独立自主的表现”“女人只有剁手才是对自己好”。
最后,资本主义依靠女性作为家中的无偿劳动力,承担抚育儿女和家务劳动,来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诸如女王节、女神节的促销活动与铺天盖地的广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类问题——用消费主义捆绑女性,用消费的意义去规范女性,这些是物化女性的更高级形式。
如何理解消费主义对女性的物化,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践行女性权益一定要从生产中去获得?为什么“劳动”才是真正的女权,而不是看你买得起什么东西?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出走后的命运: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要么饿死。原因很简单,娜拉没有工作、没有钱,“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哲学”,因此她除了出卖自己的身体就是只能向“玩偶之家”低头,可见女性的工作权力是多么的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
娜拉的困境也是当今众多女性的困境,而结论显而易见——在消费领域永远无法解决女性权益的困境。因此鼓吹什么“女人就是要做最精致的女人”“不化妆的女人就是放弃自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依然是没有脱离男权主义话语权的规范,没有掌握生产权的女性依然处在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而当今互联网一些所谓的“女权”,更是借着女权的旗号,本质依然是要把女性“待价而沽”——只不过是要装扮得更精致一些、卖的更贵一些。
李当岐教授的著作《西洋服装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洛可可时期)女性是沙龙的中心,是供男性观赏和追求的“艺术品”和宠物。男性是殷勤地服侍女性的一种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女装的外在形式美(人工美)因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博得男性的青睐和欢心,女人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装扮自己,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被紧身胸衣勒细的纤腰和用裙撑增大体积的下半身。由于紧身胸衣的长期使用,女性躯干极度变形,大大影响了健康,甚至缩短了寿命(据载当时女子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某德国贵夫人有一段嘲讽当时男性的记录:‘男人真奇妙,看着我们那装饰得很大的下半身步行或跳舞时的娇媚动作,他们两眼发直……所以,我们必须把下半身撑得更大。’一语道出了这个时期服饰美的本质,即用这种夸张的外形强调女性肉体的吸引力和美感,洛可可时期的女性均是以此为目的来装扮自己的。”
德国贵妇人的错觉在当今女性中也普遍存在,甚至有些伪女权以这种论调来标榜自己。男性竭力追求貌美年轻的女性,“殷勤地服侍”她们,让某些女性产生了自己是地位更高群体的错觉,认为只要(按男性审美)好好打扮自己,让更多的男性匍匐于自己脚下,就是践行了女性权利。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就如《西洋服装史》中这个例子,女性纵使再漂亮再性感,也不过是“艺术品和宠物”——因为她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她们不从事劳动生产,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只能把自己打扮得更精致、卖一个更好一点“价钱”。
真正的女权主义永远把视角放在劳动、生产与工作中。举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例子。让穆斯林妇女摘下头巾,这算是女权运动的巨大胜利吧,那么谁才能做到呢?社会主义国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革命后的妇女不但得到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在中亚细亚,苏联更是完成了现代社会都难以达成的任务——让穆斯林妇女摘下面纱。在这个地区,伊斯兰教数百年来根深蒂固,毛拉在当地享有至高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管理地位。妇女被当做男人的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妇女必须佩戴“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丈夫甚至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
然而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宗教中心圣波哈拉城和其他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大会发言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们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
随后妇女们在街上举行了游行,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从此当地的穆斯林女性摆脱了面纱的束缚。当地一位纺织女工写下了一首诗,遣词造句并不高明,但反映了真实朴素的情感: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与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穆斯林妇女是有什么底气摘下头巾的呢——参加了工作、挣了钱、建立了经济基础,于是就不用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附庸。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是根本性的实践方法,百试百灵。但是当今过上了优越生活的小布尔乔亚女性却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国家强行把妇女推向劳动市场,是违背了妇女自由意志,是剥削压迫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吐槽。
所以说伟大的张桂梅校长坚决反对全职太太,因为女性就算成为亿万富豪的全职太太、她老公无比疼爱她给她极其优越的经济待遇,归根到底她依然是男性的附属品,依然是这个父权制的帮凶与巩固者。
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伟大的妇女解放史。说一个模范人物:人民代表申纪兰。申纪兰奶奶堪称共和国推动男女平权最早的一代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申纪兰就在西沟村参与组织建设了妇女互助组,做布鞋棉衣被褥,组织春种秋收,开展水利建设,甚至帮前线部队修理枪支,有力的支持了八路军的前线战斗。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受封建余毒惯性的影响,妇女地位依然很低。但是,新中国解放了妇女,妇女也平等的参加劳动生产,但在合作社中却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妇女在生产队的共同劳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活、付出了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习惯上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当时叫“老五分”,而且分数记在男姓家长的名下。
申纪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遭到了男社员的普遍反对。申纪兰就提出了给女社员也划一块地,男女进行劳动竞赛,看看谁更能干。在起初的比拼中,女社员队伍落了下风,因为平时男性认为女性不会耙地和匀粪等,只能牵一牵牲口、锄一锄田地,所以女性缺乏相关技术的锻炼。而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性社员加班加点研究琢磨农活的技术技巧,反复实践改进生产方式,并一举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社员。
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西沟村申纪兰带领妇女同志战胜男同志的事迹,毛泽东主席看后非常重视,并亲自为报道写下了按语,明确指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的事例很快传遍全国,也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而当申纪兰参选本地干部、人大代表时,也受到了(主要来自中老年男性)的风言风语,认为妇女不应该如此抛头露面。对此申纪兰对妇女们说,当地有句俗话“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但在新社会我们好女也要“走到县”。随后,申纪兰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在当今世界,甚至很多发达国家中,男女同工同酬都没有法律上的保障。申纪兰推动了世界妇女人口最多的国家男女同工同酬的进程,这一功绩足以在世界女权运动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今女性的困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为生产领域,二为消费领域。而消费领域中的困境可以看做是生产领域的附属品——正是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女性受到差别对待或歧视、难以践行权益,才只能转向消费领域寻求虚无缥缈的寄托感。伪女权在消费领域大行其道、消费主义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洗脑,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于此。
在生产领域女性的困境也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在工作中,女性上升通道狭窄。女性在就业升职加薪中普遍受到歧视,认为女性“就应该顾家”“太感性不适合领导岗位”等偏见根深蒂固。对于女性过于强调自然价值(年轻、美貌),而忽略了其本身的优秀。
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对于事业有成的杰出女性用词也多为诸如“美女CEO”“美女教授”“90后女博士”这些字眼——无非还是年轻漂亮那一套。就连一款主打女性题材的综艺,竟然也对一位优秀女博士的相貌挑三拣四,仿佛女性的价值仅限于美貌。去年一个主打女性题材的国产综艺中,也充斥着诸如此类的偏见。
第二,在家庭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而绝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不会承担与女性对等的家务劳动,“丧偶式育儿”这种说法也来源于此。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女性要获得独立和与男性地位的平等,就必须要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而从事社会劳动;而女性能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条件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要有女性的一席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简而言之,脱离家务劳动、或者说男女平等承担家务、或者说女性家务劳动能够获得市场层面和金钱层面的认可,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男女平权是互为表里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的反面也可以是:既然女性的家务劳动几乎无法获得平等地对待和资本主义层面的价值兑现,那么女性生育欲望低也是情理之中,是被资本社会异化的结果。
每一位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自然必须要包括占人类总数二分之一的女性。
《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同理,女性的解放是与全人类的解放密不可分的,在推翻父权制的过程中,每一个男女都是平等的战士。女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她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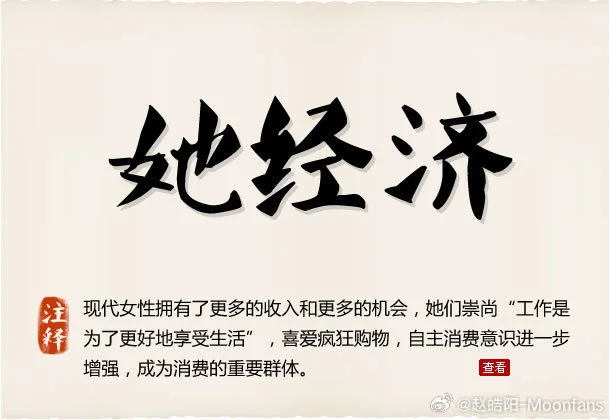


来源:赵皓阳-Moonfans
| 
